往事丨84岁才有第一次个展,他50余年绘画生涯背后有什么故事?
编者按:
写下悔过书、被迫劳改三年,与无名画会同代、在西单民主墙办展、参加星星美展集会……世事变迁,如今我们已触摸不到的往事,对周迈由来说是他们那一辈所独有的时代印记。至2020年,这位老者已手执画笔五十余年,从事艺术生涯的时间比当今许多艺术家的年龄都长,但时逢84岁高龄的他,5月份才有了其人生中的第一次个展。
大多数人不知道周迈由是谁,其参加的展览也屈指可数。现在,与其说他是一位画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这么多年看着各种艺术形式搞得如火如荼之时依旧在画点画的老人家。他从苦难中走过,比我们任何人都将更相信艺术的力量,人生的厚度也决定着他艺术的强度,在他那里,他的作品必然坚不可摧。
人生已走到这里,虽然是第一次个展,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应该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后辈,因为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失去青年,失去很多,失去老人,失去一切。前辈走过的路我们不应该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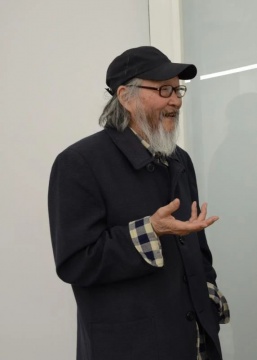
艺术家周迈由
“到灯塔去”
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周迈由是一位元老级的探索者。他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尝试当代绘画艺术,此后50余年从未放弃。在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周迈由犹如草原中的一匹独狼,孤傲不屈,独闯天下。他既不归属任何艺术流派,也从未混迹于艺术新潮之中。但是,在一些重要当代艺术群展中,却能看到周迈由的作品。例如,1978至1979年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自发展”,1979年的“星星美展”,2007年墙美术馆举办的“意派:中国抽象艺术三十年”,2014年博而励画廊展出的“85前的非官方艺术”,2017年中间美术馆筹办的“沙龙沙龙:1972-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的现代美术实践侧影”,以及2019年OCAT研究中心举办的“星星1979”回顾展等等。

1980年第二届星星美展参展艺术家合影(后排左一为周迈由)
近日,位于798艺术区的作者画廊为周迈由举办了名为“到灯塔去”的个展,展示了周迈由创作的46幅画作。这些展品的创作年代跨度非常大,从1970年创作的《心之屋·形而上》,一直到2020年3月新冠疫情期间绘制的《花火》。展览开幕后,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朱颜翠发的年轻人。在怀旧气氛浓郁的展厅中,我与周迈由做了此次访谈。

周迈由《心之屋·形而上》 253×171cm 布面油画 1970
通过有形的画作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
刘钢(以下简写为刘):周老师,我们就从《心之屋·形而上》这件作品聊起吧。它的创作年代是1970年,对吗?
周迈由(以下简写为周):坦率地说,这幅画是1969年至1971年之间创作的。我画这幅作品的时间并不长,只用了两个星期左右,但是具体年月记不太清楚了,就折中推算为1970年吧。
刘:1969至1971这三年正是文革最为疯狂的年月。您那时正好是30多岁,您有没有参与任何过激的活动?
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很害怕。记得文革初期,我在东直门大街上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大街上被一群年轻人殴打,那些年轻人拿着带有钉子的木棍追打老人,那老人被打得浑身上下都是血,惨不忍睹。我还亲眼见到一群红卫兵围着一个女人,把她身上的旗袍剪成碎片,最后那女人一丝不挂坐在地上抱头疼哭。看到这些场景,我非常恐惧。我觉得,1933年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血腥场面正在中国上演。我有些担心自己也会成为迫害的对象。政府曾经动员我到农村插队,但我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掉了。我是一个胆小的人,童年在抗日战争中度过,少年经历了内战和土地改革运动,青年参军被派到中朝边境。文革开始那些年我既恐惧又迷茫,一直有一种危机感,总觉得灾难有一天会落到我的头上。

周迈由 《包子铺》 22.4×14.9cm 纸本油画 1966
刘:您创作《心之屋·形而上》的年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期,那时的绘画都是以革命英雄人物或者大批判为题材。可是,您为什么绘出了这么一件小资情调浓郁的作品?这件作品无论在主题、情趣、表现手法等方面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并且也不符合您当时那种恐惧的心理状态。
周:你说得对。我那时处在恐惧之中。但正是惊恐、悲伤促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我想画一幅表现安宁和希望的作品,画出一个遥远、安静的世外桃源,远离动荡的社会。为了表现心中的理想世界,我采用了现代主义绘画手法。画中那个小房子是我灵魂的居所。这个房子坐落在风景优美、人烟稀少的环境中。深绿色的圆形代表树木和生命;彼此相邻、色彩不一的长条形既表现了高低起伏的地势,也烘托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远方那座嫩绿色的山岳,寓意着春天和希望;那四个蓝色的三角形既是山脉也是金字塔,它们代表着一种企盼生活永远平和的愿望。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幻想、希望、以及精神寄托都表现在这幅画中。

周迈由 《故宫》 18.8×19.2cm 纸本油画 1970
刘:您这件作品既有印象派的韵味,也有抽象艺术的元素。文革期间,这些西方艺术流派受到官方的严厉批判和打压。可是,您这件作品却表现出浓郁的西方现代主义味道。在当时,您这种表现手法是跟谁学的?
周:这样的绘画风格不是我在文革期间跟谁学的,而是在我早期艺术启蒙时留下的。我1936年出生在重庆,记得四五岁时我总是喜欢看有一位亲戚画水墨画,有时还会跟着学两笔。可以说,我是从水墨开始学画的。我10多岁时随父母搬迁到上海。我父亲有法国留学的经历,他很喜欢艺术。他看到我喜欢画画,就聘请了一位名叫迪莫夫的犹太艺术家教我画画。这位艺术家来自苏联,他或许为了逃避迫害,移居上海。这位犹太艺术家擅长现代主义绘画,我跟他学了几年油画,深受他的影响。我父亲跟林风眠有交往,50年代初他曾带我到林风眠家拜访,看林风眠画画。所以,在美学观方面,我从小就受到现代主义艺术熏陶。长大成人搬到北京后,我仍然喜欢画画,但是对学院传授的那种苏联写实主义绘画不感兴趣。虽然我很敬佩学院派的绘画技巧,但那不是我欣赏的艺术,并且我从心底里不赞成毛泽东的那套艺术理论。所以,我的绘画一直带有西方现代主义的情调。

周迈由 《香山路》 27.2×19.8cm 纸本油画 1970
刘:您为什么将《心之屋·形而上》画成大幅作品?
周: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件作品能画多大就画多大。我自己住一间平房。这么大的画挂在家中,可以给我带来安慰,让我忘掉外面那种恶劣的社会环境。
刘:文革时期,物质匮乏。您是怎么弄到这么一张大幅画布的呢?并且,您画的时候画布是怎么放的?铺在地上画的?
周:嘿嘿。那不是画布,而是一张白色的单人床单。我把它用来当成画布。画的时候,用钉子把床单的四个角钉在墙上。
刘:这件作品完成之后,就挂在家中,有没有请朋友来看过?
周:没有。就我自己欣赏。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欣赏这幅画。晚上熄灯睡觉前,也会看上两眼。那段时间,我不让任何人进我家门,担心别人看到后,会出什么意外。有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院子里喊我开门。吓得我赶紧把画摘了下来。忙乱之中,不小心把画幅右上角撕掉一小块布。为此,我心疼了好长时间。从那以后,我就把这幅画叠好,存放起来。
刘:我们聊一聊这件作品的名称吧。您什么时候为这幅画取的名字?开始画之前?绘制过程之中?还是完成之后?
周:是过程之中吧。作品画完了,名字也想好了。

周迈由 《走入莫名其妙》 80×60cm 布面油画 2007
刘:“心之屋”比较好理解,其意思是灵魂的居所。“形而上”这三个字是怎么来的?另外,您创作这件作品时,了解20世纪初以基里科为代表的“形而上画派”吗?
周:“形而上”这三个字以及画作跟西方“形而上画派”没有任何关系。“形而上”来源《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名句。按照易经的说法,“形而上”是指无形的精神世界,“形而下”是指有形的物质世界。同时,“形而上”也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含义,即有关灵魂的玄学。我将这件作品取名为“心之屋·形而上”,就是想通过有形的画作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此幅画承载了我的愿望,寄托了我的精神向往。
劳教三年,岁月的见证
刘:我听说,文革期间您被送去劳教。那是哪一年?出于什么原因?
周:那是1974年,因为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68年左右。我住的那个平房大院里有一个邻居。他解放前曾经当过地主,文革开始后被红卫兵遣送回原籍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他受不了乡下生活,没过多久就逃回北京,躲在家里。红卫兵得知他逃回来,就想把他抓回农村。为了躲避抓捕,我在家里给他挖了一个藏身洞,洞口上面放了一只沙发。只要听到院外有动静,他就跑到我家,藏进洞里。时间长了,这老兄大意了,傍晚上街溜达,被人认出,抓了起来。审讯中,他把我给供出来了。结果派出所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还叫我写了一份悔过书。这是我留下的第一个案底。1974年有人到派出所,揭发我画裸体像。一帮警察来我家搜查,搜出了好多裸体画像。这些裸体画既有我画的,也有我朋友画的。警察问我,这些都是谁画的?我说都是我画的。由于我以前犯过案,这次警察不仅收缴了所有裸体画,还把我送到天津茶淀劳改农场劳教三年。

周迈由 《夜谈》89×81cm 布面油画 2009
刘:您劳教三年吃了不少苦吧?
周:还好。我所在那个劳改大队的指导员,人挺好的。他看到我不会干活,只会画画,他就交给我写黑板报、打扫卫生之类的轻活。我劳教三年中最倒霉的一件事是遇到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大地震。我们那个劳改农场离唐山不太远。农场的土坯房全塌了,所有劳改犯都在睡梦中被砸在废墟下面,动弹不得。我们大声喊救命,有的还嚎啕大哭,可是一直没人来。被压在土坯下,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有时会听到土坯墙倒塌的声音。过了好大一会儿,救命的叫声越来越稀少。我当时觉得,我会死在这里。就在绝望之际,我隐约看到一个地方露出朦胧的光亮,仔细一看是废墟缝中透过来的晨光。那一小块天空渐渐变亮,这使我想起电影里抢救矿难的场面。我觉的有希望了,开始想别的事,其中一个就是怎么样才能把废墟缝中的晨光画出来。那天中午来了很多解放军,把我们从废墟里救出来。当然,有的劳改犯死在废墟里。
刘:您后来画过废墟缝中的晨光吗?
周:画过。那是30年之后。2007年我画了一幅挺大的画,画面上大部分是黑色的,只有小部分红色和一小长条白色,那长条白色表现的就是晨光。我把这件作品起名为《矿难》。2007年,这件作品还参加过“意派:中国抽象艺术三十年”展览。
刘:1974年您被送去劳教三年,1977年返回北京。回京后,您还继续画画吗?
周:当然继续画啦!而且,还继续画裸体像。我回京后不久,在大街上遇到以前曾经给我当裸体模特的朋友。他问我,你还敢画裸体吗?我说,这有什么不敢的。他当即就到我家,我就给他画了一幅裸体像。不过,1977年的时候,北京的社会气氛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

周迈由 《卖水者》 71×62cm 纸板油画 70年代
刘:是的。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一些。所以,1978年北京出现了一个“西单民主墙”。您好像也在那面墙上展过画吧。可以谈一谈展览经过和参展作品吗?
周:好的。西单民主墙出现以后,我常去看,最初上面很多是要求平反冤案的大字报,后来有人在那里展出画作。1979年初春,我就跟朋友宋培元一起在西单墙上办了一个双人展,展览名叫“贝地兄弟画展”。我和宋培元各自展出10余件作品。我参展作品中有一件是《卖水者》。《卖水者》表现返城知青没有工作,只能靠卖茶水维持生活。那几年大批知识青年返京,因此《卖水者》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围着看。我们在西单民主墙上的展览结束不久,马德升邀请我参加了9月下旬在中国美术馆墙外举办的“星星画展”。这个展览中,我的参展作品是一幅肖像画。“星星画展”结束后,我又与任之俊、刘秉杰等人在西单民主墙上办了一次展览,我展出了十余件作品,其中一件是《岁月的见证》。

周迈由 《肖像》 1976年 星星美展参展作品
刘:《卖水者》和《岁月的见证》是哪年画的?有人说,《卖水者》中那个男青年画的是赵文量,是这样的吗?
周:《卖水者》是1977年画的,《岁月的见证》大概是1978年画的。《卖水者》中的男青年画的不是赵文量,赵文量从未卖过大碗茶。
刘:您跟赵文量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您为什么没有参加“无名画会”?
周:我跟赵文量从60年代就认识,刚开始我们关系很好,经常一起画画,算是画友吧。但是后来赵文量喜欢搞宗派,拉帮结伙。我很不喜欢他这一点,有时候就直言不讳说出来,他听了很不高兴。再加上我被劳教三年,他也许想跟我划清界限,我从劳教所回来后,我们之间的来往就少了。但是,无名画会的展览我还是去看了。我没有参加无名画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赵文量搞山头,容不下我,我比赵文量大一岁。二是我的美学观与赵文量完全不同。赵文量提倡仿效自然,讲究调色和构图。我画画很随意,我觉得绘画是感性的,调色和构图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画作表达的内容。我的作品可以颜色不对,构图也不好看,但是只要表现出我想要表达的想法或者感觉,那就是一幅好的作品。比如我们谈论过的那件作品《心之屋·形而上》。这幅画上的山脉我画成蓝色。现实中,山脉怎么可能是蓝色的呢?但是,我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我把它们画成蓝色。赵文量已经去世了,有关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也不想说太多。

周迈由 《哥们儿》 49.5×38.5cm 纸本油画 1978
我从未颓废过
刘:好吧,理解。我们聊一聊您的绘画吧。我上次到您家,看了您保存的所有作品。此外,我还查阅了您的作品集或者群展画册。我把您的绘画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70年代到90年代。这一阶段中,您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生;另一类是“写生+”。“写生+”这一类包括《心之屋·形而上》,您参加《星星画展》的那幅肖像,还有这次展出的《哥们》。我为什么把这类作品称之为“写生+”呢?因为这类作品,您在写生的基础上,加了其他元素。您在《心之屋·形而上》中,把田野描绘为一些长条型的色块;那幅肖像画中的身躯以及身后的背景都是一些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哥们》这幅画中的一只香蕉苹果和两只花瓶上面都画有几何图形,并且这三件静物的背景还是几何图形。这些几何元素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既有抽象的感觉,也有立体派的韵味,还有构成主义绘画的情志。所以,我管这类作品称之为“写生+”。
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到现在。在这一阶段中,您的作品似乎很随意,让人难以捉摸。
周:我把自己的绘画分为三个阶段。少年的时候,什么也不懂,瞎画。从青年到中年,对绘画懂了一些,就遵从规律和法则。老年的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法则也无需遵守。就像石涛说的:“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反正我想开了。我的绘画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别人说好说坏,我不管。只要我画得开心,画得满意,那就是一幅好画。
刘:您今年84岁。从少年学习绘画一直到现在,已经有70余年了。这70多年中,是什么样的心理或者理念激励您坚持绘画?
周:我觉得,这不是我如何坚持绘画的问题,而是绘画一直在激励我生活下去。没有绘画,我活不到今天。我们这代人其实非常不走运。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时,我们未遇到过好时代。现在社会改进了,我们也老了,成了社会的累赘。但不管世道好与坏,也不管是不是别人的累赘,我从未颓废过。因为,我有绘画相伴。我有时跟我老伴说,我真正的恋爱对象是绘画,而不是你。她听了总是很生气。其实,她不懂。我和绘画之间的恋爱不是男女关系的恋爱,而是对生活的热爱。绘画对我而言就是活着。几年前参加一个群展,我在展厅的墙上写了一句话:“无论生存于何种苦难,我心中自有艺术的天国。”

周迈由 《背影》50×70cm 布面油画 2012
后记:
周迈由访谈结束后,我想起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对历史前行所做的评述:“历史仿佛是一位编年史家,漠然而执著地使一段又一段历史彼此相连,就像把一个又一个环扣串联成数千年悠久的长链,因为一切激动人心的事物都需要准备,一切重要的事件都要有个过程。”
十几年前,我在艺术史书籍中读到这么一个结论:中国当代艺术以1985年兴起的“新潮美术”为起源。对此,我曾经信以为真。后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应该追溯到1979年的《星星美展》。对此,我也曾深以为然。现在,我明白了。中国当代艺术如同长江流水一样,根本找不到源头。无数个艺术家、无数次展览、无数场论坛、无数篇艺术评论就像无数条喜马拉雅山脉上的溪流一样,最终汇集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激流。
有关周迈由艺术生涯的评价,我觉得,《人类群星闪耀时》书中的一段话恰如其分:“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点回顾那些星光灿烂的时刻,它们就像永恒夺目的星星,照耀着暂时的黑夜。”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