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少民 从美术馆的稻田里生长出来的作品
到达嘉源海美术馆的那个下午,沈少民正坐在美术馆落地窗边的桌子旁,用火烧着旧报纸的边缘。细看来,那些报纸上的新闻全都与水稻相关,甚至包括特殊时期亩产几万斤的报道。事实上,我们所在的美术馆外就是一片稻田。沈少民在这座美术馆的最新个展“米:吃进胃里的诗歌”,就是从这片稻田里生长出来的。

从稻田里生长出来的展览
行车到上海外环的嘉定区马陆镇,道路两侧的风景变成了大片的农田。由安藤忠雄设计的嘉源海美术馆便坐落在一片稻田之中。这是全世界唯一自产大米的美术馆,每逢春秋季节,金黄色的稻穗随风摇曳。这让沈少民激动不已。
作为出生于50年代的艺术家,沈少民儿时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对于大米的感情复杂而深沉。他回忆起小时候把稻粒压在手臂或手背上,在皮肤上形成花朵、太阳图案的趣事,也想起父亲为了能让家中五个孩子吃饱饭而忙碌奔波,因为偷偷开垦荒地种植的粮食被盗而默默落泪的往事。
如今大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主食,并养活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然而我们似乎没有给到它足够的尊重,甚至已经忘记了稻田是什么样子。这引发了沈少民以美术馆外稻田的产出物作为材料,包括留下的稻种,产出的大米,以及10吨的稻草,全新创作了一组有关水稻的深刻思考的作品。

嘉源海美术馆场馆全景
大脑的记忆很容易被洗掉,但是胃的记忆不会
正如安藤忠雄的建筑将7根水泥柱延伸到稻田之中,沈少民的展览也将稻田与展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互相融为对方的一部分。
沈少民稻田中那些看上去没用的稻草,送到手工做宣纸的工厂做成了宣纸。剩下的凌乱的稻草则在焚烧炉里烧成了灰,其中最细的灰做成了稻墨,每块稻墨上都有一首诗,在研墨的时候,诗歌慢慢地消失在墨里,再用这些墨在稻草做的宣纸上画成巨大的稻草,最终回归它自己。最粗的那些灰,则被机器压成了1320块墨砖,其上刻着沈少民的81首诗。这些墨砖在美术馆的入口处,被砌成了一块水稻的纪念碑。纪念碑上是沈少民的一首短诗:始终/我是我/自己的结果,背后还有一首专门写给水稻的诗。



沈少民个展“米:吃进胃里的诗歌”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在美术馆收割后的稻田里,两个由稻草编织的笼子里分别放了一只羊,这件作品充满了沈少民作品中常见的悖论:稻草本身是羊的食物,它们却被自己的食物所困扰。同样在稻田中,还有一条长150米、直径近55厘米的巨大草绳,它从户外稻田一直延伸到美术馆的中庭空间,两端各拴着若干只羊,在没有稻草作为粮食的土地上,它们可以选择吃掉稻草绳,获得自由与更多的食物。
在美术馆的展厅里,与上海自然博物馆与农科院合作的全新采集超100份水稻生长标本,收集全球近1000种稻米品种,使美术馆化身为水稻标本馆,让观众了解水稻的多样性与完整生长过程。与这些标本对应的展台上,是长达60米的手绘册页,生动地展示了水稻生长的百科全书式知识,以及人类驯化水稻、与水稻有关的神话等情景。
在展览最后,沈少民还用美术馆稻田中收获的大米,为观众准备了一锅米饭。就像他在采访中所说,“我们大脑的记忆是很容易被洗掉的,但是胃的记忆很难改变。”


沈少民个展“米:吃进胃里的诗歌”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不在艺术史的系统里做作品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这次在嘉源海美术馆的展览名“米:吃进胃里的诗歌”是怎么确定的?你关于米的记忆是怎样的?
沈少民(以下简写为沈):我在今年7月写了一段回忆,回忆我小的时候,那会儿都比较穷,粮食都是供应的,只有过年三十晚上才能吃顿大米饭,也回忆了我小时候和大米相关的一些故事,包括我父亲的经历,以及我对饥饿的记忆。我就想把我的诗歌雕刻在大米上,然后吃进胃里面,替代那种饥饿的记忆。我们大脑的记忆是很容易被洗掉的,你的观念,你的立场,你的思想都可能会被改变,但是就像东北人永远喜欢吃炖菜,四川人喜欢吃辣一样,我们胃的记忆很难改变。
Hi:这次展览完全是从美术馆外的这片稻田延伸出来的全新创作,跟你同期在昊美术馆个展中展出的旧作《中国鲤鱼》,还有之前在深圳坪山美术馆做的巨型卷尺装置《我是我自己的结果》,与空调有关的装置《被控制的自然》相比,跨度好像非常大……你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创作线索或者理念?
沈:因为我没学过艺术,所以并不是在艺术史的系统里面去做作品,我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也没有任何界限。我觉得有两种艺术家,有一种艺术家是用脑子做作品,有一种艺术家是用心做作品,我也不知道我属于哪一种,反正能触动我的东西我就会特别关注,然后才能产生好的想法。


沈少民个展“米:吃进胃里的诗歌”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艺术更应该像诗歌
Hi:你的作品中有很多类似于悖论的东西,像羊被食物困住,像尺子本身作为一个尺度,又被其他的尺子作为尺度来进行测量。这种对悖论的讨论是你很感兴趣的话题?
沈:艺术并不是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你的作品还要去追问一些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让大家去思考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我觉得它更应该像诗歌。我的作品跟诗歌没什么区别,有的时候是根据作品写首诗,有的时候是根据诗做了一件作品。
Hi:你的诗给人一种直接的感受,有时候甚至只有一句话,就像稻草纪念碑上的那句“始终我是我自己的结果”。
沈:我不喜欢绕来绕去,好的作品不是说有多高深,让人很难懂,有时候可能他自己都没懂。
Hi:刚刚我们谈到的那件《中国鲤鱼》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00条机械的鲤鱼在工业盐上面跳动,分不清是真是假。那件作品当时创作的由头,或者说让你特别触动和关注的点是什么?
沈:在中国鲤鱼其实是一个吉祥物,过去贴的年画里都是一个大胖小子骑着一条大鲤鱼,或者鲤鱼跃龙门,这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在2017-2018年左右,锦鲤这个词在网上特别火,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搜索了一下。因为鲤鱼有清理水质的作用,所以美国和加拿大引进了,效果很不错,但是问题是它的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特别强,破坏了生态平衡,跟我们网上流传的锦鲤完全不同,它变成了一种灾难。这也跟这些国家的移民问题非常相似。


《中国鲤鱼》35.6×14.5×6cm/条×2000
机械、塑料、硅胶、电子呼吸系统、盐 2018
坪山美术馆展览现场
机械、塑料、硅胶、电子呼吸系统、盐 2018
坪山美术馆展览现场
Hi:为什么最终的呈现形式是2000条鲤鱼躺在一堆工业盐上?
沈:你细想盐是让人很绝望的,像海水晒干之后的形态。当时有一篇报道写这件作品,说沈少民用17吨盐腌了2000条咸鱼,或者解读成咸鱼翻身什么的,跟我的想法完全是两回事。
Hi:你会拒绝大家的这种误读吗?
沈:我挺喜欢看那些误读,有时候比我的想象力还丰富。



沈少民个展“米:吃进胃里的诗歌”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我是一个靠直觉做艺术的人
Hi:你作为东北人,在80年代就到了北京开始做艺术家,1989年之后去了澳洲,现在常驻深圳吗?
沈:我现在的工作室还是在北京,深圳和北京两地跑,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北京没有以前那么好玩了。
Hi:为什么?跟你在80年代所处的北京有什么不同?
沈:那时候中国处于思想上刚刚解放的时代,现在回看,无论是诗歌还是摇滚的辉煌时期都是在80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是从那时起步的。那会我也没写诗,但整天跟那些诗人混在一块儿。到了1989年之后我去了澳洲,但没有真正在澳洲待过,也是断断续续的,在澳洲和北京两头跑。



沈少民个展“米:吃进胃里的诗歌”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Hi:我现在看到你比较早的展览或者作品是2007年的那几个大型的装置《一号工程》《盆景》《磕头机》《歼-X》……那时候已经回国了吗?
沈:我是2002年回来的。2007年做的三个个展也都是巫鸿策划的,在今日美术馆、站台中国、四合苑画廊、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这次展览是巫鸿策划的我的第四个个展。我记得当时还参加了唐人北京的一个群展中,很多艺术家做的作品都比较实验,展厅分成了两层,下面是一个暗室,没有光线。艺术家黑羚羊找了一个外科医生,把自己的身体划开再缝上,把黑暗缝进自己的身体。那会儿比现在好玩。那天我也跟巫鸿聊,他现在很少做展览了,很多艺术不好玩,不能让他激动。
Hi:无论是2007年的大型装置,还是前面提到的《中国鲤鱼》,那种巨大的体量带给人一种很大的震撼。你作品中的这种基因是从哪里来的?
沈:我是一个靠直觉做艺术的人,我也不会考虑太多观众给我作品的定义。对我来说做作品震不震撼,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系,或者跟年代有关系。比如80年代诗歌圈摇滚圈的那种愤怒和呐喊,也许变成一种语法习惯了,而不是说我特意去追求什么。在今天的年轻艺术家那里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可能也不需要,现实也不允许。

《盆景》展览现场
第17届悉尼双年展 2007
第17届悉尼双年展 2007
我也可以不是艺术家
Hi:对于非科班出身的你来说,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了?
沈:我现在也没有非得定义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我做的事别人觉得是艺术,那就是艺术作品了,要是觉得不是,我也可以不是艺术家。用自己的语法去讲一些想讲的故事,我觉得挺好玩的。
Hi:所以你的创作并不局限于当代艺术这种表达方式,还包括诗歌、纪录片等很多不同形式。
沈: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无法定义,能定义的都不是当代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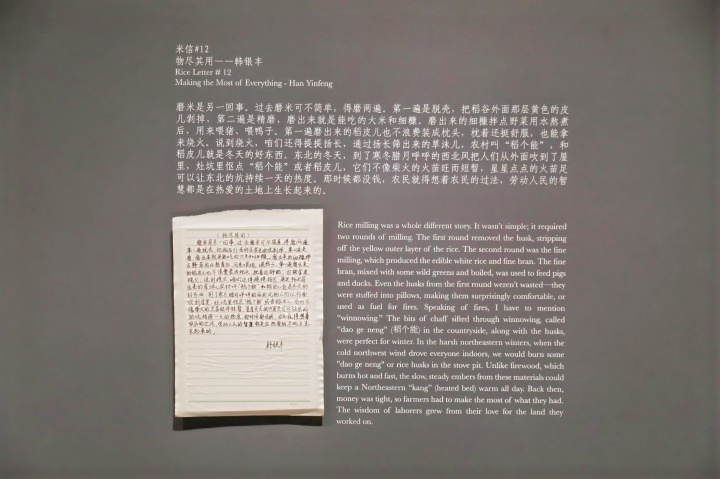

沈少民个展“米:吃进胃里的诗歌”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嘉源海美术馆展览现场
Hi:你现在的身份还是深圳大学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同时也是科学艺术联合实验室的艺术总监,公共艺术和科学跟艺术的结合是你感兴趣的方向吗?
沈: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公共艺术的表达会更加自由一些,因为它是跟大众直接对话的艺术,考虑的是跟城市的关系,跟环境的关系,跟点位的建筑关系,以及跟人的互动关系,它没有那么多风险,是现阶段能做的一些事情。
科技艺术现在比较流行,但是对于流行的东西,我一般都会很警惕。我做的科技艺术方向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看过很多科技艺术展,大多数都是在炫技,弄得眼花缭乱,看上去就像一个科技产品展。当然也有做得很观念的,很智慧的。我觉得科技艺术本身就应该带有对科技质疑的这样一种态度,艺术家一定是走在科学家前面的人,因为艺术是启蒙,科技是改变。所以我们实验室会把科学家放弃的或者失败的一些方案接过来做,给出一个感性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一首诗,也可能是一幅画,一个装置,或者一个影像。
Hi:你刚刚提到公共艺术是现阶段可以做的事情,现实中会遇到一定的限制吗?
沈:我们的艺术家已经被训练得即使没人限制,自己都先自我审查了。中国艺术家已经做到不让上面操心了。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