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森伯格给中国艺术留下什么遗产?
2016年6月11日下午,大型展览“劳森伯格在中国”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罗伯特·劳森伯格是战后美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受到黑山学院先锋实验实践及纽约晚期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他发展出一种个人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实践——融合绘画(Combine Painting)。他使用美术拼贴技法,将废弃的家常物件、商业产品、印刷品等等组成抽象的画板画。可以说,劳森伯格打破了传统绘画和雕塑的界限,扩大了艺术表达的材料、媒介,劳森伯格说:“我希望在事物未经完全显露的情况下呈现出其复杂性。”

罗伯特·劳森伯格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俘虏岛的工作室创作《四分之一英里画作》(1981–1998),1983。图片由罗伯特·劳森伯格基金会档案馆(纽约)提供。摄影:特里·凡·布伦特
这次展览展出美国的劳森伯格(1925年—2008年)的作品《四分之一英里画作》(The 1/4 Mile or 2 Furlong Piece, 1981年—1998年),该作品由190部分组成,长度约305米,这是该作品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展出。同时展出还有劳森伯格的拍摄于1982年访问中国期间的彩色照片《〈中国夏宫〉研究》(1983年)。 在艺术史上与劳森伯格同等重要的艺术家很多,不得不说比他重要的艺术家也不乏其人,但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却是独特的。1982年夏,劳森伯格到访中国三周,中国之旅同时也推动他建立劳森伯格海外文化交流会组织(ROCI,1984-1991年)。为了这个流动的艺术制作及展览项目,他离开美国造访10个国家,以广泛收集材料、拍摄照片、结交当地工匠并展出自己的作品。1985年,他回到北京,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ROCI中国”。当时这场展览正值中国当代艺术兴起之际,参观展览的艺术家将展厅挤的满满当当,栗宪庭说:“在经历了70多年写实主义审美教育之后,劳森柏格的个展确实给中国艺术界带来一次不小的地震。” 劳森伯格给85时期亲历展览的艺术家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将如何再次面对劳森伯格呢?
注:因不同时期翻译原因,文中所提劳生柏,劳申柏,劳森伯,劳森伯格均为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

栗宪庭:资讯的输入和中国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资讯有时会起到催化剂或者中医所说药引子的作用,诸如七十年代末期日本艺术家东山魁夷画展之于中国风情油画风,1985年劳森柏个人展览之于中国达达、和现成品热潮,1987年塔皮埃斯展览之于中国综合材料画风。当然,给中国艺术界影响和刺激最大的当属劳森柏的个人展览,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资讯,中国艺术的情境,以及恰当的时间,三者缺一不可,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契机。 1985年10月份,正当中国现代艺术潮流风起云涌之时,劳森柏到中国美术馆开了个展,展览期间,来参观展览的艺术家把展厅挤得满满的,而且整个展览期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虽不能说空前绝后,但在我的记忆里也是中国美术馆少有的盛况。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在经历了70多年的写实主义审美教育之后,劳森柏的个展确实给中国艺术界带来一次不小的地震,无论是包装箱,还是动物标本,无论是装置,还是现成品,劳森柏的每一件作品,都让大多数中国观众看得一头雾水,就是相当数量的艺术家,在劳森柏的展品面前也倍感困惑,现代艺术史中的经典疑问:这是艺术吗?也成为中国观众的疑问,这种疑问的价值,在于劳森柏的作品开始触动中国观众的审美意识,起码中国人开始知道艺术还可以这样搞。当然最重要的是,劳森柏的作品,起到了给如火如荼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火上加油的作用,它让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原汁原味的西方达达以后的现代艺术,对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来说,劳森柏的展览来的太及时了!因为,1985年,不但是中国现代艺术潮流――85新潮的高峰时期,同时,整个中国的文化界正兴起了文化批判热,在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身上正蓄积着对中国传统――无论是古代文人画传统还是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的批判热情,中国有句俗语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劳森柏的作品――尤其是其中的装置和现成品样式,刺激着中国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无怪乎,一夜之间全中国的现代艺术新潮中开始玩起了现成品,当时尽管对劳森柏的作品有些误读――其实误读一向是文化承传和影响的基本规律,一是当时中国缺乏商业和消费文化的背景,整个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批判和反文化热潮,二是劳森柏的作品本来继承了达达的语言因素,西方艺术史也把早期波普叫作新达达,所以,作为波普艺术大师的劳森柏,被中国年轻艺术家误读成达达也是自然的。那时最著名的现代艺术团体如厦门达达,杭州的红白黑小组,山西的现代艺术展览等都是受到劳森柏的影响而发生的。尤其是红白黑小组的作品,那是一组带达达意味的波普。当时还是学生的吴山专带头和他的同学倪海峰、马海舟等人创作了《红50%、黑25%、白25%》的文字作品系列,把《白菜三分钱一斤》,《居委会》等日常生活中无知、琐屑的俗语,用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口号般的大标语样式表现出来,在大量的红色中配以黑色和白色,使作品具有简洁而暴力的色彩。我甚至认为,吴山专开创的达达式波普和西方消费文化的波普样式,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幽默关系,同构即大众化、流行性、肤浅、充满热情。异质即一个是革命和暴力;一个是温情和幽默,我似乎觉得它们是人性由于冷战的不同语境,所表现出的对立而又孪生的一体两面。不仅如此,它还为后来在中国出现的“政治波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先导作用,从吴山专从波普转换出文革群众标语符号,到王广义并置文革符号和商业符号,其中起作用的是消费文化的社会背景的出现,1990年代初,西方消费文化乘中国经济改革的东风,迅速渗透到中国的各个领域,以王广义为代表的政治波普迅速表达了这种生存感觉--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顷刻间被西方消费文化所重创的幽默感觉。这一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但是,劳森柏的展览来得真是太及时了!
注:1985年劳森伯格在北京的展览结束之后,《中国美术报》用了一个整版介绍劳森伯格,而栗宪庭正是那期报纸的执行总编,并且用李家屯的笔名撰写《劳生柏给严肃的中国观众开了一个大玩笑》一文,2008年劳森伯格邀栗宪庭为他的中国展览写文章,文章写完之前,劳森伯格突然离世,文章也成为了对他的一种怀念。本采访由作者提供稿件,文章题目为《劳森柏和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契机》(有节选)

隋建国:1985年劳生伯展览来京时,我刚大学毕业一年,还在山东济南。那几年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年都要在秋季来北京看展览,若遇上重要展览还要专门来看。劳生伯展我记得是专门跑来北京看的。那时正根据自己对于老庄和禅宗的理解,尝试建立一套工作方法来做雕塑。也用这些作品参与了山东那边的青年美术运动的一些展览,成为其中的骨干。 劳生伯的作品给我的震撼是很大的。他作品中形象、图像或者物体的偶然相遇,并不甚至故意回避它们之间的意义、比喻、象征关系,材料造型上的逻辑也减少到最小。也是沿着劳生伯的线索,我开始理解约翰.凯奇以及黑山学院等一系列文化艺术潮流。实际上也是一次逆向的理解中国禅宗的过程。这里所谓“逆向”是指,从“波普”,劳生伯,黑山学院,凯奇,铃木大拙,日本禅宗,向中国禅宗的反向解读过程。这样的过程,有利于理解不同文明或者文化圈之间,概念传播—误读—极端化,并进一步转化为新的文化艺术能量的过程。 实际上,1986年我就来到北京,卷入了85、86艺术与文化的思潮中,思想情绪的震荡,已经超出了劳生伯展览所带来的冲击,思维与作品完全进入了政治与情感的层面,成为现实政治与个人情绪的对应物。这种状态后来一直持续到1996年。这期间的作品,充满着隐喻与象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可那种,说我这期间作品有日本物派影子的说法,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时期的作品是与我对当时社会与个人命运有着血肉联系的产物,哪有物派那样的“寂静”与超越? 今天劳生伯的意义或许在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圈可以借此反思:后现代艺术为吸引大众参与而背离早期现代或者经典现代艺术原理,推崇作品内容和图像以及象征,将人类学和社会学加入到艺术实践与解释过程中的普遍影响。三十年是不是一个轮回?

张晓刚:对于劳申柏的思想及作品,我一直有种纠结,究竟是喜欢他呢还是欣赏他呢还是因为欣赏他不得不喜欢他呢?随着艺术界对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己也许并不应该喜欢他,但是又绝对的欣赏他认可他,因为无论如何,在80年代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家对世界的认知渴望远远大于文化判断的时期,是他第一个给中国艺术界带来了一次从观念到视觉的革命,连同后来的塔皮埃斯,使我们绝大多数的艺术家都对“现成品”,“材料”以及何谓“自由表达”等等有了深刻的现场感受和认识。当时大家似乎有一种对绘画的内容对像乃至材料和工具及表达方式都开拓起来了,尤其是有不少艺术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也较之过去更多地开始脱离书本化的影响。当然这些还只是某种技术层面的表面影响。至于劳申伯作品中所隐藏的关于政治和历史的内涵直到九十年代才开始被真正关注到,那也同时得益于德国新表现主义如巴塞利兹,基弗尔等人的警醒。 很遗憾我当时正在忙着为调到川美去工作而积极表现努力上课中,没去成北京一睹现场,听叶永青看完展览回来激动地转述,也跟着小澎湃了一阵。这种对自由和颠覆的渴望与当时国内的人文背景十分贴切,而与川美以乡土现实为主流艺术创作的氛围格格不入。劳氏的展览就像一针吗啡,让我们这小群喜欢现代主义的人既兴奋又有点不知所措一一兴奋者乃感受到被某种自由与创造的冲动所激励,不知所措则因为对我们仍然在迷恋于表现主义绘画的人来说突然有了某种莫名的迷茫,毕竟这种对追述杜尚以来的现成品理念与大众文化的美国式随性混搭来得太迅猛了。这对我们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遵循的欧洲现代主义传统,尤其是以德国和法国文化为榜样的人来说,正处于强烈的模仿期,虽然表面上也会尝试学习使用一些材料拼贴等技术,但美国文化中所包含的那种戏谑与轻松随意有时令我还有某种隔离感,甚至有时还会觉得浮浅和过于直白。直到进入九十年代我似乎才开始真正理解美国波普文化。所以我有时会认为劳申柏所代表的美国文化,通过此次展览开始真正意义上在改变长期以来以俄罗斯文化以及欧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化”对中国的深层影响。 今天在中囯重新回看劳申柏等老牌艺术家的作品,抛开“大师”的光环和资本市场豪华的外套,当他们的艺术语言已经不再闪烁着当年的革命性光芒时,当那些当年的“垃圾”现成品都已成为博物馆中的经典时,他们作品中所传递出的智慧与率性的力量,还在穿透时空的云层令我们感动么?能够继续启发我们去不顾一切地寻求自身文化价值的呈现么?回答如果是肯定的,那才真是我们的福份了。

叶永青:1985年的冬日,阳光遥远而冷冽,我在中国美术馆的门廊迎面遇上大名鼎鼎的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劳申柏!他硬朗的影子在美术馆的大厅门口拉得好长……那时,他巨大的个展正在这里展出,这是一个使一个刚刚开放的国度震惊㓆陷的展览,劳自称全部作品用军用运输机从世界各地将作品运至北京和西藏,在其看来,军人最理想的作用就是保护艺术与文化,在他的文化想象中,他曾经饲养的小乌龟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带领他的艺术在全球巡展,信奉艺术改变世界的他最为著名的名言是:“共享不同,世界如此亲切!”最酷的是,在每一地,动用不同国家的军队为艺术家搬运作品布置画展。在劳申柏看来,才是一种人类最美好的工作象征。 劳申柏对我的启蒙几乎是转折性的,他说:“如果我能画出或者制造出诚实的作品,它所体现出的所有这些成分就是现实。我的作品必须至少看上去跟窗户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样有趣才行。”从那时起,艺术不再只发生于诗和远方,不只局限于书本化的完美与正确的方式,更不消非要在遥远的云南和西藏边地风情中寄托和汲取源泉。在北京冬日暖气管道和臭哄哄的冻白菜堆集的小屋里,我的画面上第一次出现了原本厌恨逃避的重庆发电厂的烟火世界⋯我突然开悟:原來艺术也可以置于周遭和日常,无奈的现实也可以与人如此亲近爱痛交加。重要的是在生活与艺术之间获得的那份诚实的游戏感,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图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通过艺术告诉我们,人生也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不论对錯,不分等級与富贵贫贱——而是将有趣置于正确之上的直觉和勇力。这个感悟,我视为劳申伯匮赠终身的礼物。 我至今仍保留着他赠送給我的两张签名印刷,那时劳申柏身旁跟随着三位身材威猛的保镖,而那时的我,只不过是一个闻讯而来,初涉艺术的懵懂青年,单薄、瘦弱,因未吃早餐而饥肠辘辘,我的全部家当只是行囊里的一瓶水和一份准备作为午餐的煎饼果子,以及一本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为追寻艺术的“真谛”和扺抗当时如日中天庸俗的主流绘画四处漂泊,行走于西双版納、圭山和西藏……劳申柏和他带来的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席卷并洗刧了我以及一代人匮乏的视野。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以及影响至深的创作启迪。今天,这些回忆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消逝,那些劳申柏关于艺术与生活转換的创作启示也仍然在当下成为值得面对的问题!

徐累:劳森柏对我没有产生影响。因为他还是一个有现实干预度的艺术家,提供了现实主义的新方法,可能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劳森柏的展览我更想看一看他处理中国题材的作品,从他的角度,当时是什么中国原料吸引他,怎样表达他的新鲜感,可能能勾起我们记忆的那部分。 我对劳森柏记忆深的是1991年,当时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举办的一场慈善拍卖预展,有不少国际有名艺术家捐赠,用以修复长城和威尼斯,劳森柏也有一件作品,好像是当时价格最高的。

王音:1985年我上大二,去看劳森伯展的时候,感觉像是给开了脑洞。因为之前,我对战后美国艺术了解并不多。那个展览,给了艺术界的一个启迪,让大家直接看见了,艺术可以有各种可能的搞法。当时这个启发,可以说影响深远。我也是那个时候,开始通过书本,对战后的西方艺术有了些知识性的了解。时隔30年,“劳森伯”又一次回来,对大家来讲有点故友重逢之感,UCCA在这个时间做这样一个展览,或许用心良多,让大家重访一下“劳森伯”,也重温一下我们过往。

朱青生:劳森伯格之所以伟大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对中国有重大的贡献,我们中国人凡是对自己有恩情的人都会崇敬他,劳森伯格就是这样一个人。另外一个方面因为他对艺术的贡献,这一点在艺术史上已经有定论。 劳森伯格早期的时刻你们知道,他是一个波普艺术家,但是更早的时候他是黑山学院的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艺术家。 今天我们不是要看一件好看的作品,更不是看艺术家生平,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史只有艺术家,这种说法早期叫做明日黄花了。因为我们今天不是看艺术家,也不是看艺术作品,而是看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面对我们自己枷锁的时刻敢于突破它,挣脱它。而劳森伯格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做了榜样。而且他这个榜样如此杰出,就是因为当一个枷锁还没有形成枷锁的时候,他已经寻找到了突破它的理由,一生保持着对它的警惕,这种精神在我们中国最有意义的最需要的一种精神。 虽然他已经过世,但是这种精神,在艺术界作为比较杰出的代表,依旧飘扬在我们大家的上空,是有昭示性,昭示性是我们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因此他到中国有双重的特征,最早来到中国是跟着波士顿美术馆过来的,只有他一件作品,我们当时到波看展览的时候,先看古典艺术的部分,然后我们听到一个故事,当时中国因为对于当代艺术或者叫现代艺术不了解,于是只想展出古典的部分,不愿展出当代的部分。 当时的策划人是波士顿美术馆馆长,他当场做了一个决定,要么都展要么不展,于是在中国美术馆,第一次有了现代艺术的部分。而这个里边最重要的一张作品就是劳森伯格的作品,他的作品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墙面上2楼一个展厅里面的侧面,旁边是光从窗子打过来的,就是几个铁锹靠在墙上,这张作品一下子使得人们对于艺术是什么产生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和想法。 紧接着到了1985年的时候,劳森伯格的作品就能够进入中国来展出了,11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在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留校当老师了,因为我是1985年2月份开始当老师的。11月份的时候,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我的学生中有刘小东,方力钧,展望这些人。我记得把他们带到展厅里边去上课,那么这一次展览和之前展览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展览是他的一次个展,在这个展览中间不仅展出了他的全部的一种想法,而且把怎么做展览,艺术家怎么面对艺术,把这件事情完整呈现的在大家面前。 今天我们赞颂劳森伯格,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感恩的心态,对于一切对我们有过重大影响的人都会去赞颂他。我们会说这是85美术运动的启动者,这个时间上不太对,因为85运动是1984年1985年已经有,劳森伯格进入中国的时候是1985年底,中国已经有了85美术运动,劳森伯格来了以后启动了1986年30年前那一次转折。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一些艺术家,已经清晰的意识到当代艺术并不是某一种艺术,或者某一种风格,更不是西方的艺术,而是每个人必须直接面对和直接创造的一种可能性。 在1986年的时候,中国的一批年轻人,当时我30岁不到,在中央美院当教师时,就决定要建立现代艺术大展。现在大展第一批筹备材料就存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中国现代艺术档案里。这是原来当时筹备的情况,但是这个展览由于一些政治原因没有能够展出,一直拖到1989年才展出,你们就能想象这个事情是多么的重要。 那这一次转折点在哪?我觉得就是劳森伯格对中国的贡献,他告诉我们艺术其实不是一样东西,艺术是所有的东西,作为艺术家应该寻找到对艺术的解释,而不是创造一件艺术的作品,这就是劳森伯格对中国的意义之所在。
注:本文节选自6月6日于北大讲座《UCCA走进大学系列——谁是劳森伯格? 》

宋冬: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那时候门一开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进来了。对那种新鲜空气的感悟,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1985年刚刚开始上大学,在这之前没有过类似的展览,他使用了全方位的空间,媒材非常广泛。当时看到他的作品,对我而言有很强的冲击,感觉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可以非常自由的表达,用各种手段去呈现。后来通过书籍就对他的了解非常多了,今天我们再重新看他,需要用不同的目光,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实验性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进入美术馆进入美术史的经典艺术家了,更需要挖掘的是他经典性的一面。这次的展览对我而言,代表的是一种对劳申柏的崇敬。这三十年,在我最开始大学生涯的时候,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新鲜空气。

费大为:1985年我从中央美院毕业留校,并开始和国内的前卫艺术家联络。正在兴起的85新潮运动的主要成员都是美院毕业生,在美院可以看到大量国外艺术杂志,关于当代艺术的翻译著作也已经出现,所以我们对劳森伯格的作品并不陌生。85新潮中的主要潮流如“北方群体”,“厦门达达”,“池社”,以及主要艺术家的基本面貌已经形成。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因为劳森伯格展览而出现转向。我自己去看这个展览时,也没有感到期待中的震撼,却意外地感觉到一种莫名的隔阂和距离。劳森伯格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幽默和洒脱,是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向波普艺术的过渡。而1985年的中国前卫艺术所思考的问题正好缺少行动绘画和波普艺术这两个环节(而1988年以后在中国前卫艺术出现波普倾向,更多是从安迪·沃霍那里受到的启发),1985年劳森伯格的作品已经比他年轻时更多了一些矫饰主义的味道。这种矫饰主义味道对当时正在发狂的中国前卫艺术家来说未免过于典雅。 劳森伯格展览对中国前卫艺术的影响主要是山西的现代艺术七人展。劳的展览1985年11月18日在北京举办,一个半月以后,完全模仿劳森伯格的山西现代艺术七人展就出现了。劳森伯格对那些以前较少接触过当代艺术信息,同时又尚未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艺术家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对劳的模仿主要也是形式上的激情模仿,这种模仿对他们以后的创作并没有持久的影响力。 劳森伯格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我们不应该无限夸大1985年那个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前卫艺术圈子看来,这个展览的重要性主要是释放了一个政治上的信号:刚刚从极左的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中解脱出来不到一年,北京的官方美术馆竟然允许举办这样的展览,说明了重新开放的势头将会迅猛地到来。 顺便还可以一提的是,劳森伯格1985年的展览无疑也是在当时特定政治形势下以极快的速度匆忙策划出来的。策划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位住在美国的华人女士,我忘记她的姓名。不知这次劳森伯格的展览有没有提到这位女士的工作?在当时极端封闭的形势下,没有她所做的工作,那次在北京的和在西藏的展览根本无法实现。 记得一个细节:在那次开幕式上,和我一起看展览的朋友拿着相机在展厅里拍照,这时冲过来一个人高马大的美国人对他大吼起来。这是劳森伯格的助手,他很快被那位华人女士拉走,并向我们道歉。能听懂英语的朋友对我说,他说,“如果我发现你在外面发表你的照片,我就fucking拧断你的脖子!”其实展厅里并没有张贴请勿拍照的牌子。 与此同时,展厅的另一头,劳森伯格正在和中国官方的美协官员们一起开座谈会。我能想象,劳森伯格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劳森伯格的艺术在今天看来是一次美术史的展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看待一个艺术是否有现实意义,不在于观看的对象,主要还在于观看者自己。任何艺术史上的创作都可以是今天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任何最新的创作动向,都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结束。所以看古代艺术展览要像看当下艺术展览那样去看,看当下艺术展览应该像看古代艺术展那样去看,这样看展览才会看得有意思。

王兴伟:1985年劳生柏的展览的巨大影响是因为那时中国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对具体作品的理解不理解是次要的,它相当于发出一个信号弹:要当代、什么都可以作为艺术。这有点象"走向当代"的一个发令枪,因为“当代”这个概念不是一直存在的、这个概念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全新的概念,等于开启了新空间。 劳生柏的作品拼凑了很多原素,组合方式比较随机和跳跃,是移动和发散式的,你是没法追踪他的思路的,是很难理解,或者说用"理解"这个概念是很难接近他的作品的,不是因为深奥。一方面会感觉他的作品思路层出不穷、左右逢源、天马行空;另一方面又会感觉空洞无物、不知所云、松松垮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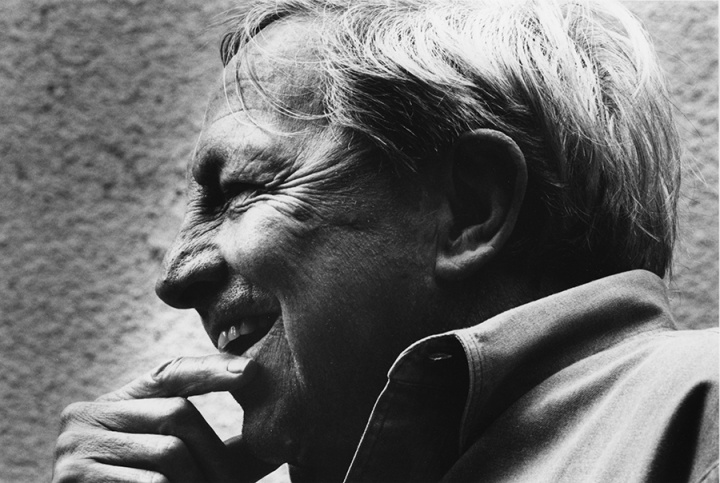
马可鲁:劳申柏是1985年来中国展览,展览第二天劳申柏来外交公寓参观。当时是在北京的外交公寓何模乐家中举办的“七人画展”,其中参展艺术家有张伟、顾德新、王鲁炎、朱金石、秦玉芬和我,好像还有冯国东,我们每个人都有六七幅作品。当时官方安排他去美术学院,他没去,来到我们这里。他喜欢我们的作品,当时我有四幅作品是抽象的,两幅是比较具象的。我们谈到所面对的困境,劳申柏对我只是说放下包袱,开放思路。当时我们对官方的一切都不关心,因为劳申柏的作品同时正在受到官方的欢迎,占领了整个中国美术馆,也出于一些别的心态,所以提问的时候,张伟就提出说你的展览像原子弹一样引起这么大反响,但你的作品没什么价值。劳申柏回答说:“艺术家不批评艺术家。” 对我来说,劳申柏的作品对我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真正喜欢的不是他的作品,我形容他更像一个拳击手,觉得他代表一种美国精神,所有的东西都很张扬,并且敏锐的选择各种材料,能力超群,他的材料更多的是视觉语言的延伸,和现在的装置是有区别的。对我来说可能当时更喜欢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当时劳申柏的作品还是影响了很多人的,包括黄永砯、徐冰。但今天的情形和当时也不一样,如今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大,在艺术上会有很多独特的地方。

王鲁炎:当年我们北京的一帮现代艺术家在外交公寓举行的一个很小的群展,劳申伯格一行来看了我们的展览,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的作品没有对我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一定会有潜在的影响。时隔30年后,我故地重游,又一次在外交公寓举行了一个很小的个人展览。这个展览的意义对我而言,在于又有机会在一个硬件条件很不专业的“业余”的展览空间里,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较为纯粹地以小展览和小的作品的方式与较少的观众进行交流。这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公寓艺术”呈现方式在今天的展览语境里具有纯粹性与精神性的象征性意义。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