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 香格纳画廊是一种精神
画廊向来是一门特殊而又复杂的行当。

只要在一个地方开个空间,
它就会自己生长
这家由瑞士人劳伦斯·何浦林(Lorenz Helbling)创立、在中国本土深耕的初代画廊,去年遭遇了多位骨干员工离职,北京空间暂停关闭的风波。
或许香格纳的这段插曲,也是多数画廊从0起步再到发展壮大,迟早要迈过的一道坎。只不过,有着近60位合作艺术家的香格纳,比国内其它画廊的规模更大、历史更长,也就更早一步遇见了这些棘手难题。

2024对香格纳来说,又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北京空间在暂停一年后装修重启;再过一两个月,用了近九年的上海西岸空间也即将搬离,何去何从,仍旧未知。
“先解决眼下的问题,”劳伦斯说自己从来不是一个有严谨逻辑的人。空间的开辟也一样,无论上海、北京还是后来的新加坡,他都更着眼于当下。“我一直觉得,只要在一个地方开个空间,它就会自己生长。”
在香格纳北京空间重启亮相的前一周,劳伦斯来到了北京。空间正处在装修的收尾阶段。我们坐在硬件全新升级的画廊的中庭,谈话就从曾梵志当年在院子里种下的眼前这棵紫藤开始……

见证了北京空间15年的变迁
(摄影:罗颖)
2008年,在上海经营了12年画廊的劳伦斯,在曾梵志的“怂恿”下进军北京,两位老友在草场地做起了邻居。这份邀约也正合劳伦斯当时的心意,他想借此契机扩大香格纳在北京的影响力,同时兼顾北京合作的艺术家们。

希望香格纳在北京也能成为
一家有影响力的画廊
“你如何评价香格纳北京空间在过去15年的表现?”我问劳伦斯。
“它的影响力似乎不太大。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年决定要改变的原因,我希望它在北京也能成为一家有影响力的画廊。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无论香格纳在业界的成绩有多出色,劳伦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过去几年里,几位生活工作在北京的70、80后中坚艺术家与香格纳开启了合作,然后又陆续离开。
是这家来自上海的画廊在北方水土不服?还是有其它不足为外人道的难言之隐?
“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也不要解释太多,可能是发展的一个阶段,”劳伦斯用他依然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到。“我想回到原来的路——艺术第一,第二是为艺术服务。”

开一个画廊很难
香格纳的英文名为ShanghART,这个词提供了许多联想空间:Shanghai Art、The heart of Shanghai……而在德语中,hart还有“很难”的意思。“所以,开一个画廊很难,”劳伦斯说。
ShanghART最初来源于劳伦斯瑞士老乡的一句玩笑话:有一天你会在上海开一个画廊,画廊的名字就叫“ShanghART”。那是1985年,劳伦斯还在复旦大学进修。

十年后,一个叫ShanghART的画廊在上海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二楼开业了。“开了两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开心死了。我们居然还活着!两年,二十年,再到一转眼近三十年”。劳伦斯坦言,开画廊从没有过安全感。但也因为始终伴随的危机感,他从未停止对好艺术家的寻找。
寻找这个时代有意思的人
从一开始,艺术就是劳伦斯生活的全部。他的父亲和弟弟都是艺术家。父亲师承自包豪斯的一位老师。弟弟的朋友圈则是像皮皮乐迪·里思特(Pipilotti Rist)、米里亚姆·卡恩(Miriam Cahn)等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们。那个圈子就在劳伦斯身边,只是,他们都与自己无关。
在苏黎士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修完历史、中文和艺术史后,劳伦斯找到了一份在软件公司的职务。“无聊的工作”,劳伦斯如此形容。后来他放弃了这份不错的收入,去了香港工作。1995年,劳伦斯再次返回上海,就此扎下了根,创办了这座城市的第一家当代艺术画廊。
“法国在20世纪初有新的艺术形式,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有活跃的艺术氛围。我隐约觉得属于中国当代艺术的那个时代也即将到来。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艺术家,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他想去寻找这个时代有意思的人。于是,就有了劳伦斯90年代的上海街头骑着自行车给客户送画,一手扶车把,一手拿画的画面。但这段故事,已经是过去式了。
接下来的三十年,劳伦斯和他的香格纳又将怎样去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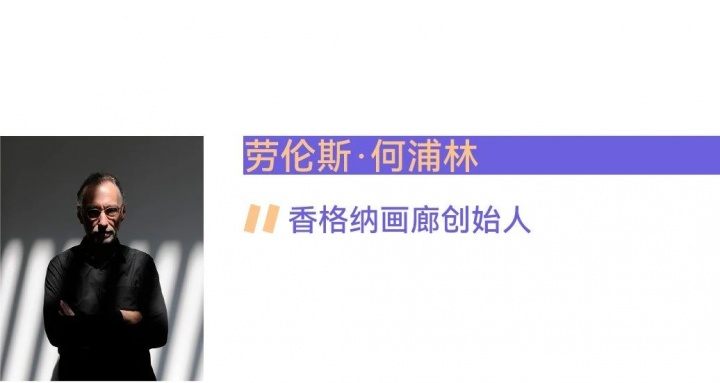
每十年就会遇到一次改变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香格纳北京空间暂停一年多的原因是什么?
劳伦斯·何浦林(Lorenz Helbling)(以下简写为L):我们似乎每十年就会遇到一次改变,之前也有人离开。二十年后,又有人离开。对我来说也是偶然,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也不要解释太多,可能是发展到了一个阶段。但我们会继续推我们喜欢的艺术家,走原来的路。
Hi:原来的路是什么?
L:艺术在中心。当然生意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艺术是第一,第二是为艺术服务。
L:一半一半。2020年3月我们在纽约有个博览会,但当时美国和中国的航线断了,我就先回到瑞士。9月回到了上海。然后2021年都在上海。2022年6月去了瑞士Art Basel,2023年1月才回来。所以差不多各一半。
L:在国外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和上海保持着沟通,但很多细节没办法决定。当时我希望画廊大的方向还是要安全一些,不要做太多有风险的尝试。所以做什么展览基本上都定好了,其它的细节就交给他们去做。毕竟合作了20多年。疫情结束之后,大环境正在向稳定的方向发展,我觉得画廊可以回到原来的路,继续做更多有意思的展览。
L:先活下去,是疫情期间大家的共同目的。我也很紧张,担心客户不买东西,但他们也很支持我们。疫情那几年我们做的都是比较有名的艺术家的展览。余友涵、丁乙、曾梵志、张恩利他们给了我们相当大的支持。但同时也停滞了许多画廊该做的工作,比如出版、支持年轻艺术家,以及做很多不一定卖得好、但必须要做的展览。那段时间团队很不容易,做出了成绩,总算渡过了难关。但现在我们要回到香格纳画廊该有的样子,我们得回去。
L:我不知道放弃哪些部分。从读书到工作,都是围绕艺术这一件事,花了很多力气,它是我生活的全部。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很累。
需要更聪明的管理办法
Hi:你怎么评价香格纳北京空间在过去15年的表现?
L:它的影响力似乎不太大。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北京有空间,或者艺术圈觉得它好像不那么重要。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年决定要改变的原因,我希望它在北京也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画廊。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L:因为之前我没办法做。
Hi:那时候上海和北京空间在定位上有什么不同的侧重?
L:我们确实一直在讨论北京可以有什么定位,是要做年轻艺术家吗?但我没有这个想法,我想的就是做好艺术,做好画廊。

Hi:你多数时间都在上海,目前来看与香格纳最“长情”的艺术家大部分也是在上海及其周边城市,那如何维护在其他城市的艺术家关系?
L:我始终认为香格纳有今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也没有刻意安排它的发展。艺术家、藏家也给了我很多建议。所以对北京最初也是这个想法。但现在看来,如果我不在这边,可能需要更聪明的管理办法。
Hi:有什么好的办法?
L:或许需要找到合适的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发展画廊,了解艺术家的需求、客户的需求,以及这座城市需要什么。L:或许需要找到合适的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发展画廊,了解艺术家的需求、客户的需求,以及这座城市需要什么。
Hi:但很多艺术家会更看重和画廊主的直接交流。
L:我原来觉得不需要。现在看来,是个大错误。这肯定很重要。不过我觉得也可以有替代方案。画廊的同事也都需要和艺术家打交道,去工作室和他们沟通。这也是他们的工作里最有意思的部分。只要对艺术有兴趣,别人也可以做这个部分的工作。而不是我不在了,画廊就没了。我肯定得想个办法,让它延续下去。香格纳画廊是一种精神,不光是我一个人有,别人也可能有。
Hi:所以你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画廊。
L:虽然当时取名字比较随意,但我很明确画廊不要用我的名字。它是一份工作,当它步入正轨后,我可以从中抽离。
L:法国在20世纪初有印象派新的艺术形式,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有抽象表现主义活跃的艺术气氛。我来到上海,隐约觉得属于中国当代艺术的那个时代即将到来。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艺术家,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我不想带着过去的偏见去看他们,而是要在他们所处的时间去观察他们,看他们的作品。
Hi:你怎么选艺术家?
L:我不会选某一种风格,也不会考虑某一种媒介,也不关心是不是年轻。我就是要去找这个时代有意思的人。90年代的上海没有画廊,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了解艺术家。比如丁乙, 1993年我在威尼斯看了他的作品,1994年又在香港看到,观察了两年才确定跟他合作。
之后在莫干山路M50附近有了七八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我离他们很近。平时就可以很随意地去看工作室。后来大家都忙碌了起来。但上海还是会时常见面,北京就来得少了。
艺术家只要做好的作品,
我们就会好卖
Hi:现在呢?最近有计划去走访一些在北京的艺术家工作室吗?
L:有计划。一方面我会尽量多来北京,另一方面也会鼓励画廊同事多去了解,形成一个网络,哪些人我们可以去关注,也不一定非要年轻。比如我们去年就在新加坡找到了一位80多岁的艺术家唐大雾。
L:我和徐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才20岁,认识鸟头的宋涛的时候他也还没毕业。我们现在对年轻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谁知道呢?看看以后吧。90年代我看了那么多艺术家,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把他们都放在一个“锅”里。有的人跟90年代没什么关系,反而跟60、70、80年代关联更大。
你看丁乙的老师是余友涵,邬一名也是他的学生,魏光庆是曾梵志的老师。耿建翌是杨振中、张鼎的老师。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会帮助你理解他们的作品。这跟年龄无关,但跟理解作品有关。
L:过去30年,香格纳合作的基本上都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但现在肯定会要关心在国外成长的华人艺术家。
Hi:跟年轻艺术家打交道会不会有代沟?
L:我的中文也不是那么好。从语言沟通的角度来说肯定需要时间,但我和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沟通不是很难。
Hi:会给艺术家作品提意见吗?
L:不会。我也在学习。但现在画廊那么大,即便我不给人提意见,艺术家可能也觉得和画廊合作就得做好卖的作品。我觉得艺术家只要做好的作品,我们就会好卖。所以我们尽量不给意见,让艺术家自己发展。


最理想的是每个人
都抱着“冒险”的心态
Hi:在画廊经营策略上,你会考虑实验性强、但不那么挣钱的展览比例吗?
L: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展是不打算挣钱的。我们肯定想成功,想卖出去,只是会遇到比较难卖掉的作品。但我们不会任性地为了名气,做3个不卖钱的展览,然后又做3个卖钱的展览。我们也想帮艺术家卖掉作品,而不是利用他们做广告。这不是一件好事。有些作品很难卖,但我们还是卖得掉。这也是画廊生意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楼下做一个实验性的不卖钱的,楼上做卖钱的展览。
Hi:对你来说,心目中的完美藏家画像是什么样的?
L:我们最理想的是每个人都抱着“冒险”的心态。艺术家不要根据市场来改变他的作品,一门心思做好作品就行。画廊负责找最好的作品。收藏家也一样。既然是“冒险”,就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100个人里,肯定不都是最好的。收藏当代艺术肯定要胆子大,你要靠自己的感觉,理解这个时代。我们处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的时代。
Hi:这么多年来,香格纳画廊的藏家结构有发生变化吗?
L:过去肯定是国外的藏家多。不过疫情开始发生了改变,中国藏家在变多,也更重要。过去中国观众看艺术的机会少,但这些年明显多了观看的渠道。他们现在更容易判断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第一次来我们画廊的客户可能当年才15岁,但现在45岁了,他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是如何发展的全过程,他们对本国艺术家了解更深入。西方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丁乙还是一位新人。还有一个变化是,原来以国外的私人收藏为主,现在西方的美术馆慢慢开始研究中国当代艺术了,他们最初对中国都不感兴趣。
L:我的感受是国外有些艺术家的发展比中国快多了。有的人在5年内就从0蹿升到几百万美金,他们可能连美术馆的展览都没有。但我觉得这个不那么重要,就让他们做吧。我们现在说的一些中国艺术家,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有至少20年历史,所以我觉得中国艺术家不算贵。但实际上大多数艺术家发展得很慢,都在辛辛苦苦地过日子。
永远没有安全感
但有助于找到好艺术家
Hi:画廊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L:艺术家也会很孤独,画廊就是站在TA身边的人,帮他打开空间,给作品展示的机会,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尤其是新的艺术,它需要更多的时间。
Hi:作为画廊主,你最喜欢画廊众多繁琐工作环节中的哪个部分?
L:我喜欢什么都不做(笑)。其实都喜欢,比如我也喜欢布置展览,喜欢跟艺术家沟通。但有人比我做得好,我就会让有能力的人去做。所以不要破坏有能力的人。
L:看我(笑)。肯定是开放、敏感,也需要不停地怀疑已知的东西。他要知道他可能会失败,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L:开画廊那么不容易。当时开了两个星期已经高兴死了,怎么我们还活着?开了两年、二十年,一直都没有安全感。一方面好作品卖掉就没有了。蒙娜丽莎只有一件,卖掉就没了。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达芬奇,再找第二个达芬奇。每次都会否定原来找的艺术家。它不像卖咖啡,你可以继续做继续卖。你要不停地去找好的作品,好的艺术家。所以永远没有安全感,但它也会帮助你找到好的艺术家。
Hi:如果请你给现在要开画廊的人提供一些建议,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Hi:在画廊行业三十年的得与失分别是什么?
L:画廊的名字还在,这是最大的“得”。没有遗憾,这是美好的30年。

香格纳M50空间
Hi:如果从1995年开始算,你来中国也近30年了,你怎么看过去这3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
L:过去三十年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阶段。难得有那么多国家互相沟通,全球化的交流,有竞争也有学习,每个人都需要考虑“我是谁”。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